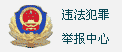○風滿樓
家山馬古蘭
在馬古蘭,丘東平的家。
穿堂的風,隨我開鎖、推門進入這座清時“上三下三”的門廳,我聽到,風掠過凹門斗檐下烏石制的門框、門檻,還有關刀狀的出拱。風,拋下陽光獨照在天井鋪地的烏石板上,舊構其實沒有改變,從前的往事心事在陽光下顯影,粉刷過的窗欞脫落,露出原來灰沙的細節。
披鶴發的母親,倚門企盼,盼來的是,兒子譚月的故人。聶紺弩的一首七律,以文字捕捉了這一刻,用文字為母親的望兒歸畫了像。天井的烏石板隨陽光,邁過門坎,探進廂房,發亮的包漿,刻錄著東平的時光。我不忍踩下,怕留下影像的劃痕。
傍村而過,為塵土荒草掩蓋的惠潮古道上,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的東平走過,青年、中年的我走過,足印部分重疊,我在時間的這一頭。時間的那一頭,馬蹄聲遠。
風,隨我轉身鎖門關門停滯,留下一段往事。
故園東山
速生桉終于不前,斷續之間,竹、樟、鴨腳木以清晰的分辨率出現。起落的石徑,鏈接了百年前的時光,一把鋒利的鉤鐮,重啟了鐘敬文的故園東山。
壘石之上,夯土殘留,一副老朽的三間過舊厝痕跡,在石徑高處停頓。山楂、紅柿、杜梨、柚子、柑橘,石徑深處的伯公小廟,鐘老少年時的詩聲,還有我多年前的記憶,在高大的古荔身后隱匿。人聲一時溢滿園居的遺址,填補了日常的蒼涼,我的到來,只是鉤沉一些歲月的碎片。
薇甘菊以菊的香氣,掩蓋絞殺的意圖,正在樹間伺伏,我分明嗅到了它傳遞的信息。我聽到了荔枝、龍眼的喘息、嘆息,在我身后響起。鉤鐮斷開的路徑,悄悄愈合,揭開的幕,枝芽萌發,在腳步走遠之后緩慢閉幕。
蘭窗小記
鳥不經意間泊來的馬櫻丹,流瀑般掩飾了瓦片陷落的尷尬與狼藉,填補了天空的留白。蘭窗還在,黑漆漆的一方木橫欞,深邃與我對視。只須把一籃吊蘭掛上,似乎故事便可復原。
我設想悄無聲息潛入這鐘老故地,翻越坍塌的矮墻,落地惹了碎瓦發出的斷裂聲,引出一流竄的貓,一聲凄厲的叫聲,還是打破這處廢居的平靜。厝與天井的邊際已模糊,在雜亂中,只有一方露頭的旗桿夾,提示著斯文的存在。窗外的天井,遍地瓦礫,坍塌的墻還原成了土,我須以跳躍的代價,方能換取眼前這一幕。
上三間下三間間斷一天井,前后與雜貨街魚街吻合,實、虛、實間的布局如“離”卦,鐘敬文青年出走之后再也沒有回來。如一枚擱在海灘上洞穿無數孔的螺殼,螺、蟹先后寄居其間,惟獨留下軀殼,以殘缺慢慢抵御時光的侵蝕。而我,剛發好就著這午后的陽光,目睹這樣一個消逝的片段。
馬思聰的長巷
東向的門樓轉折,三間三進連同西側的附厝,速寫般勾勒馬家祖居的宏大敘事,這只是一角。鳥屎落下榕,沖天而出,盤根錯節間取代后座東廂的屋宇。厚重的麻石門框、立柱、出屐、臺階,保留著步步高升的進深高遠,可以想象的精美木雕缺席,依然一副大戶人家的架構。散落橫放的旗桿夾,記錄著富貴的來處去處,鐫刻著財富的刻度,如一把標尺,靜靜躺在墻的角落,風吹雨曬。前廳中廳的屏門,只遺下石柱礎,卯位空洞,充滿對榫合還有木構的念想。
馬思聰最初的琴聲,以口琴、手風琴的形式,在這里悠揚響起。以門樓轉身的長巷,隨四十九塊烏石板鋪墊、銜接,如鋼琴的黑鍵,半音演奏,在海豐歌謠的吟唱、白字戲的清唱、朗朗的讀書聲、算盤撥動珠子上下的清脆聲中,匯進熙熙攘攘的幼石街市聲里,直到《思鄉曲》響起,一曲成讖。琴聲是對長巷的回饋與致敬,這長巷太長,終其后半生,馬思聰再也無法返回涉足。
多年以后,我以鞋履叩響,這四十九個馬思聰無數次叩響過的黑鍵,空巷足音,何以勝道?耳際是蒼涼的四野,依山的落日飛雁。






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
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