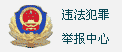○陳丹玉
天還未亮透,窗外漏進第一聲鳥鳴,濕漉漉的,像從深夢里掙脫。這時,小妹推門進來,喊:“老大,快起來,襟德路要收攤了。”我翻個身,床板的吱呀聲替我應著。
海城,這座小城是慢慢蘇醒的。豆腐老陳的三輪軋過水泥路,投早市的大媽大叔的腳步聲和笑談聲悠長悠長,大街小巷,各家店鋪的拉匝門次第打開。晨光如潮,漫過獅山市場、老市場、海悅路,銅錢山路,停在襟德路的早市上。
七點五十分。這條路沸了。
海鮮攤前,海蝦塭蝦在塑料布上蹦跳,濺起細碎水珠。一個大媽蹲著討價還價,手指卻專挑弓著身子的肥蝦。“再便宜兩塊嘛。”她抬臂擦汗,袖口深了一片。賣蝦婦人只是笑,笑容藏在帽子底下。
旁邊的魚攤,喇叭循環喊著“十元一斤”。斑豬魚瞪圓眼睛,蘇君魚鱗片閃著銀光……殺魚的漢子手起刀落,魚鱗如雪飛濺。他兒子——約莫高中生的年紀,高高瘦瘦,帶點拽,低頭稱重,碎發遮住眉眼。妹妹蹲下挑魚,手指輕按魚鰓:“要這條,還有那條。”她說要買二十斤,帶回東莞,慢慢吃。那少年抬頭,眼睛亮了亮。
我的心忽然軟了一下。這場景太熟悉了——十年前,母親也是這樣蹲在魚攤前,手指輕輕按過每條魚的鰓蓋,口里喃喃說:“鰓鮮,日子就鮮。”
香芋攤前,一對古稀老夫妻,配合默契。爺爺稱重,奶奶削皮。有個大媽要付錢,老奶奶把二維碼藏到身后:“拿去吃啦,不要錢,不要錢,唔大事(沒多少錢之意)。”原來她們是幾十年的老鄰居。我看著老奶奶佝僂的背,想起母親生前也愛這樣,把最新鮮的芋頭塞給鄰家。
蓮藕攤的姑娘抬頭時,麥色臉龐像初秋的稻穗。我問她藕是哪里挖的,她說:“笏口。”我心一陣暖,我的村子。想認親,可見她忙得滿臉汗水,終究沒有開口。她彎腰整理蓮藕時,發梢滴著汗,那姿態,讓我想起年輕時的母親,在自家田里挖藕的樣子。
妹妹買東西的神態,活脫脫是母親在世時的模樣。看見什么都覺得好,魚要最鮮的,蝦要最活的,時蔬要最嫩綠的……不到二十分鐘,我們已提著三四十斤收獲。妹夫弓著腰提著兩大袋,汗珠順鬢角滑落,笑容卻像初升的太陽。
人聲嗡嗡,我有些恍惚。那些擦汗的、討價的、彎腰挑選的身影,都像是本世紀初的母親。她也是這般胖胖的,攥著手帕,擦著汗,看見什么都說好。“這社會越來越好。”她總愛這么說,眼睛瞇成兩條縫。如今滿街都是她的影子,唯獨沒有她。
買夠了,我們帶著一身魚腥味回到小區。早餐攤老板娘認得我們:“還是豬雜粿條?”十五元一大碗,湯是奶白色的,浮著翠綠芹菜末。我們坐在塑料凳上吃,熱氣蒙住眼鏡。這味道淡淡的,一直沒變過,就像母親的手藝。
換了身衣服,去舅舅家。還沒進門就聽見擂茶聲——哐啷哐啷,像心跳。舅媽在擂缽里放了油柑,酸澀過后泛起甘甜。風從陽臺溜進來,搖曳室內的綠植。舅舅說起老表們在珠三角工作生活的事,舅媽說起外孫子已讀初中,她可以不去廣州表妹家了,我聊起暑假旅游的見聞……喝著咸茶,油柑的余味在舌尖。
傍晚忽然起風了。云從海那邊壓過來,黑沉沉的。霓虹次第亮起,小區像披了綴滿珍珠的衣裳。六歲的侄女趴在陽臺喊:“大姨,前面放戲了!”雨后初秋的夜確實涼快,空氣里都是濕潤的草木香。
小廣場上,投影儀把光影投在瓷磚墻壁上。《狀元與乞丐》的唱腔在夜色里飄蕩。負責投影的大叔說,大家湊錢買的設備,“已經放了二十多天啦”。他指著前排的老人,“他們不愛看電視,就愛聚在一起看戲,白字戲,西秦戲,有時也播放《紅樓夢》和《三國演義》等老劇”。
大媽們邊看邊低聲議論,大爺們專注地跟著哼唱。孩子們看不懂劇情,安靜地坐著,偶爾回頭看看打盹的老人,偷偷地笑。我家那小侄女坐在第一排,神情專注,背影小小的,真真像個老戲迷。
夜風習習,榕樹葉子沙沙響。投影的光束里,塵埃緩緩浮動。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在村里看戲,也是這樣的夜晚,也是這樣的涼風。只是那時的戲臺是臨時搭的,現在的戲臺卻在天地之間。
戲還在唱,人還在看。從清晨的魚市到夜晚的戲場,日子就這樣不緊不慢地流過。而有些東西,就像海城的襟德路上那些老攤子,始終在那里——任憑臺風來過又走,云聚了又散。






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
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