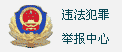○蔡贊生
陸豐河西街道的巷陌如細(xì)密交織的蠶絲,將市井煙火勾勒成工筆長卷。各式黃底藍(lán)字的店牌在縱橫交錯間星羅棋布,恍若漁火點點的港灣標(biāo)識。后坑路段的喧嘩聲里,有一間專營“河西鴨糝”的飯店招牌懸于飛檐之下,霓虹燈箱在暮色中泛起暖光,像極了舊時藥鋪門前的招子——這本就是一味療愈鄉(xiāng)愁的方劑。

《南齊書》中的“鴨臛”二字在紙頁間沉睡千年,竟在南海之濱的這個小鎮(zhèn)化作氤氳熱氣。陸豐河西人的“糝”字其音義近似“散”字,暗合“散百病”“散厄運”的古老讖語。清末瘟疫流行時,郎中教人將整鴨連骨搗碎熬湯,分食防疫的典故,如今已化作石臼底殘渣傳向四方的傳說。老人做壽時分送“百家鴨糝”的習(xí)俗,讓這道小吃超越了食饌之趣,成為連接天地人倫的媒介。
后坑路段的飯店店內(nèi)圓桌不規(guī)則排列,宛如展開的山水手卷。我擇角落坐下,對著系圍裙的老板笑道:“來碗鴨糝湯!”話音未落,后廚已傳來石杵撞擊石臼的悶響,恍若遠(yuǎn)古部落祭祀的鼓點。這聲音讓我想起父親年關(guān)搗鴨糝的場景——兩只肥鴨在青石臼中漸漸化作肉糝,木杵起落間迸濺的不只是鴨肉纖維,更是整個童年對年味的全部想象。
白瓷大碗端上時,乳白湯液中浮沉的鴨糝如灰龍游弋。蒜苗蔥花撒作青白星子,生姜粉漾開胭脂般的漣漪。夾起一筷抿入口中,鴨糝在舌尖掀起鮮味的浪潮,蔥花的暖意順著食道滑入胃囊,仿佛窗臺突然照進一束陽光。那若有若無的胡椒辛香,恰似嶺南雨季飄過窗欞的微風(fēng),捉摸不定卻真實存在。
老板拎著湯壺過來添湯,閑談間,說起本地人用石臼搗鴨糝的掌故。他談起,光緒年間其祖上在汕頭港得了一塊南洋船運來的花崗巖石,請潮州石匠鑿了三個月才成石臼器皿,用了多少代人了,家人一直愛吃自家搗的鴨糝。“現(xiàn)在的人多用機器打漿了,但村里也有人過年還得請出老石臼,不然一些老人家就會覺得不用石臼搗的鴨糝就沒了魂脈。”他摩挲著柜臺邊緣包漿的木紋,“去年有個印尼老華僑尋來,說夢里都是石杵聲,捧著碗里的鴨糝哭得湯都涼了。”
這讓我想起北宋的《東京夢華錄》里記載的“搗珍”,古人早知機械力擊打能改變?nèi)赓|(zhì)結(jié)構(gòu),河西人吃鴨糝一直都相信石臼搗出的鴨糝藏著天地精氣,老一輩的人還堅信是石頭記憶著千百次捶打中融入的祈愿,“吃了平安順。”
店外摩托車、電動車載著保溫箱穿梭如織,快遞小哥的吆喝聲與石杵聲交織成奇妙的二重奏。現(xiàn)代物流讓鴨糝得以真空包裝發(fā)往四海,但離開河西地界的鴨糝總少了幾分韻味——或許差的不是水質(zhì)火候,而是缺了河西后坑路段嘈雜市聲的浸潤,缺了木棉樹影落在湯碗里的斑駁。
有個戴眼鏡的年輕人進來要了二十份真空包裝:“廠里陸豐老鄉(xiāng)湊單的,在東莞總做不出這個味。”他守著師傅打包時說起趣事:去年中秋他們在外務(wù)工的十幾人湊錢買了石臼寄過去,結(jié)果物業(yè)當(dāng)違禁品扣下了。“最后只好用破壁機打,總歸不是那個勁道。”
我曾聽村里一個叔公說起往事:大饑荒時他的祖父用最后半袋米換鴨熬糝,喂得染疫的的他緩過氣來。“現(xiàn)在孩子們總說膽固醇高,他們哪知道這碗湯救過咱家三代人。”
這些故事讓碗中的鴨糝漸漸沉重起來。它不再只是滿足口腹之欲的食物,而是變成承載集體記憶的容器,盛著這片土地上人們的悲歡離合。那些分散厄運的古老祝禱、固元氣的養(yǎng)生智慧,在現(xiàn)代社會依然以味覺形式延續(xù)著生命。
老村還有人家保留有一個完好的石臼。青石內(nèi)壁被歲月打磨得溫潤如玉,杵頭裹著綢布靜靜立在角落,仿佛隨時準(zhǔn)備喚醒沉睡的肌肉記憶。我忽然明白父親為何過年一定要吃鴨糝:那反復(fù)捶打的動作是在模仿大地心跳,石與肉碰撞的聲音是獻給山河歲月的頌歌。當(dāng)現(xiàn)代生活將一切精細(xì)化、標(biāo)準(zhǔn)化,我們依然需要某種粗糲的儀式來確認(rèn)自己與土地的聯(lián)系。
碗中游弋的豈止是鴨糝,分明是山海之間的元氣流轉(zhuǎn),是代代相傳的生命密碼。愛吃鴨糝湯的鄉(xiāng)人心里或會藏著一只石臼,在城市的深夜發(fā)出沉悶回響,提醒著來自何處,歸向何方。






 粵公網(wǎng)安備 44150202000069號
粵公網(wǎng)安備 44150202000069號